汪寅仙《曲壺》震撼了一個時代

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汪寅仙,以超凡的境界,卓越的藝術成就,早己馳名遐邇,譽貫中西。作為大師級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,肩擔天降之大任,紫砂花器大作似立體的畫、有形的詩而意境深遠,耐人尋味,以文心雕龍,達天成之道,在陶藝界旗幟飄揚,獨領風騷。她與張守智先生合作的“曲壺”,用辯證思維和夢幻般的想象力,“曲則全,枉則直”的理念,簡約虛實的立意,氣勢如虹的架構,創作了無愧當代陶藝重器經典,一把壺震撼了一個時代。
歷史造就了英雄,英雄創造了時代。華夏文明博大而糟深,從伏羲太極根脈,先人摶土柴火成陶,開啟文明曙光,五千載積淀厚重,形成了儒道“尚仁貴和”“道法自然”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,在求知求善,返璞歸真,自然唯美中實現著社會和諧中庸。在我們這個民族心靈的最深處,寄托著與天地共生,同山水共處的無限情感。人們在簡單、樸實的認知中,用平凡的人生,勤勞靈巧的雙手,推崇著陶土藝術的素樸之美,揭示著古老哲學的最高境界——天地人和。

一把泥土,一名藝術家,一件作品,于火成陶,胡玉胡金,或實用或欣賞,成為了中國的符號。紫砂是陶之精華,丹青寫厚德,書畫可載物,與傳統文化一路同行,修得君子般溫潤品行,置用清賞世間為首,天下文人寵愛有佳。紫砂藝術幾百年來,在偶然與必然之間,在大巧與大拙之間,在大雅和大俗之間,記載著百姓的悲歡離合;記載著江南文人的風花雪月,記載著陶都人的勤勞與智慧,記載著藝術家傳奇而動人的故事。
汪寅仙大師作為當代紫砂藝術的杰出代表,她的從藝經歷、美學思想、藝術構思、作品的造型和色彩等,都對紫砂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,承前啟后,開花器雅美一代新風,碩果累累,集陶藝之大成。她把光器的書卷素雅,花器的生動情趣,用女性特有的眼光,敏感而細膩的手法,進行了絕妙的結合,花器之文雅,光器之靈動,放大情感于作品之上,在精神上追求至誠至美,她的作品總有出人預料的藝術效果,如音棲弦,如煙成靄,環肥燕瘦,淡菊幽蘭。汪大師終日不倦,得其妙理,陶藝致廣大而盡精微,極高明而道中庸,用通神之功,力追鳴遠,她是紫砂界又一座藝術高峰。

出身于制陶世家的汪大師,自幼玩泥,孩提時就對紫砂有天然的親近感,她特別的興趣和感覺,多次得到祖母和母親的夸獎。當年僅十四歲還帶糟幼稚的汪寅仙來到工藝廠,真正成為一名紫砂人時,并沒有引起別人的在意,一樣的分班,一樣的上課,簡陋的條件,窘促的廠房,在吳云根老師的指導下,她開始了謹慎地徒承之路,未料想三年未滿,便嶄露頭角成為小輔導,在當時,已經顯現出她日后必定成才的天分,開始被刮目相看了。朱可心作為汪寅仙從藝路上的一代思師,名師得高徒曾一度傳為佳話,這是一段難忘的歷程,老師的贊賞,學生的勤奮,從“圣思桃杯”開始,報春壺、冬梅茶具等,每做一件作品,都是一次成功的綹登,當紫砂葡萄杯、風卷葵壺、大彎鏨梅椿壺完成出爐時,敢做敢為的汪寅仙已經初露鋒芒,名聲大噪了。積跬步至千里,積小流至江海,恩師的教誨,永遠激勵著大師的腳步。幾十年過去了,老師早已作古,學生業已成為備受矚目一代工藝美術大師,善變創新,天下取則。他創作的藝術作品,不論光貨花貨,器若鐘鼎,釋放出了征服般的藝術魅力。老師列他的影響是一生的,已經化為了一種豪氣和精神,做人正直,做壺端莊,友善親和,充滿愛心,汪大師用這寶貴真傳,打開了神圣的藝術法門,躬耕在陽羨溪頭,遴游于紫砂藝海,她創作的紫砂藝術之美,如詩如畫,分外妖嬈,讓天下人為之驚嘆。

一把“曲壺”,為陶都續寫了嶄新的篇章,贏得了久遠的美譽,引來了無數的青瞇,當代的很多青年紫砂收藏家,就是從見到“曲壺”開始的,那動靜相宜的現代之美,沉穩端莊的肌理質感,代表著一種哲學,一種文化,代表著一個民族的審美,和現代人生活的追求。作者用一根侗單的曲線,在上下貫通,旋轉流動的立體軌跡中,勾勒出了一件完美的造型,用紫砂泥的特性,使壺的寬度、厚度以及角度恰到好處,俱成天趣。這啟蒙于《易經》“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”,來自于同源的筆墨丹青“畫貴有神韻,有氣魄,然皆從虛靈中得來”。細細解讀“曲壺”的造型語言,在空間與實體的強烈對比中,它承載著厚重的歷史掌故,表達著無數的現代信息,用古人之規矩,而抒寫自己之靈性,在文化藝術的傳承中,乘風破浪,永立湖頭,無疑成為當代傳世經典,新時代的“諾亞方舟”。

“曲壺”的巨大成功,觸發了汪大師創作的激情,打開了情感的閘門,猶如春江放舟,一泄千里。先后創作了“松竹梅壺”、“黑松壺”、“圣柏壺”、“仙桃提梁壺”、“神鳥出林壺”、“斑竹蟬衣提梁壺”等優秀作品,一把壺一段動人的故事,一件作品一幅絕妙的詩畫,藝術上的每一次突破,都凝聚著是大師的心血和智慧,藝術上的每一次成功,大師的境界總會得到一次嶄新的升華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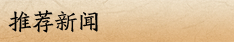







 滬公網安備31011202007513號
滬公網安備31011202007513號
